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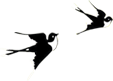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引言:作为文化密码的笔墨系统
当张大千泼彩山水在拍卖场以亿元成交时,当实验水墨以装置形态出现在威尼斯双年展时,当代中国画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身份焦虑。这种焦虑本质上是农业文明孕育的笔墨语言在数字文明语境中的价值重估。从北宋郭熙"三远法"构建的空间哲学,到倪瓒"写胸中逸气"的笔墨自觉,中国画的精神内核始终植根于"心性——笔墨——自然"的三元结构。然而在全球化与技术主义浪潮下,这一延续千年的文化系统正遭遇三重撕裂:传统笔墨程式在学院教育中被解构为造型技术;文人画的精神高度在市场逻辑中被降维为视觉符号;自然观照的哲学深度在图像复制时代被异化为媒介实验。本文将从文化基因断层、教育体系异化、市场机制规训、技术伦理困境四个维度,系统剖析当代中国画创作的困局本质,并从心性哲学、人文养成、创作机制三个层面,重构以"笔墨心性论"为核心的当代创作体系,最终在传统文脉与现代性体验的张力中,探寻中国画的精神复归之路。
一、文化基因断层:传统笔墨的现代性失语
(一)哲学根基的消解与审美范式的断裂
中国画的笔墨系统本质上是儒道释哲学的视觉化呈现。"气韵生动"的审美追求源于《周易》"阴阳相生"的宇宙观,"留白"的空间处理暗合老子"有无相生"的辩证思维,而文人画"逸品"的境界则直接承接禅宗"明心见性"的精神指向。这种哲学与艺术的深度耦合,在明清文人画中发展为完备的"心性——笔墨"转化机制:董其昌以"南北宗论"构建的笔墨谱系,实则是将禅宗顿悟思想转化为绘画语言的方法论;石涛"一画论"中的"一画",并非单纯的技法概念,而是"从于心"的宇宙本体论在绘画中的投射。
当代中国画的文化困境首先表现为这种哲学根基的消解。20世纪初"美术革命"以来,康有为"合中西而为画学新纪元"的主张,虽推动了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却也埋下了文化基因断裂的隐患。徐悲鸿引入的西方学院派写实体系,在改造中国画造型能力的同时,也将"应物象形"异化为科学透视下的客观描摹,导致"迁想妙得"的写意精神逐渐流失。至20世纪80年代"85新潮",西方现代主义思潮以更激进的方式冲击传统,部分艺术家将中国画解构为纯粹的视觉形式,吴冠中"笔墨等于零"的论断,虽有打破程式化僵局的积极意义,却也在理论上抽空了笔墨的文化内涵,使中国画沦为无本之木。
(二)笔墨本体论的式微与符号化陷阱
传统中国画的笔墨具有双重属性:既是造型手段,更是精神载体。荆浩在《笔法记》中提出的"筋、肉、骨、气"四势,将笔墨提升至生命美学的高度;黄宾虹"五笔七墨"的技法体系,实则是通过笔墨节奏模拟宇宙运行的韵律。这种"笔墨即心性"的本体论,在当代创作中逐渐被边缘化。
在市场逻辑主导的艺术生态中,笔墨沦为符号生产的工具。当代的"新工笔人物画"将传统的工笔画的线条简化为装饰性轮廓,在唯美主义表象下抽空了"传神阿堵"的精神内涵;某些"所谓的新文人绘画"创作者将八大的简笔造型异化为程式化符号,以"丑怪"风格迎合市场对"传统趣味"的想象性消费。这种符号化倾向导致笔墨丧失了"立象以尽意"的功能,沦为没有灵魂的视觉空壳。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实验水墨艺术家受抽象表现主义影响,将笔墨解构为纯粹的肌理效果,用喷枪、拓印等技术替代毛笔的书写性,使水墨沦为媒介实验的材料,背离了"墨分五色"中蕴含的生命节奏。
(三)自然观照方式的异化与精神空间的萎缩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是中国画创作的根本法则。传统画家对自然的观照并非客观描摹,而是"澄观万象"后的心灵映射。范宽居华山数十年,"山顶好作密林,水际作突兀大石"的画风,实则是将华山的雄浑气象内化为笔墨语言;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记载的"以大观小"法,打破了西方焦点透视的局限,构建了"俯仰自得"的宇宙式观照方式。这种观照方式形成的精神空间,正是中国画"可游可居"审美体验的根源。
当代画家对自然的认知方式发生了根本转变。数码相机与写生照片的普及,使画家不再需要"饱游沃看"的沉浸式体验,而是通过照片素材进行拼贴组合,导致画面失去了"对景造意"的生命律动。更严重的是,工业化进程中的自然景观异化,使传统山水画的"山水精神"失去了现实载体。当张家界的奇峰异石被纳入旅游开发的视觉符号体系,当黄公望笔下的富春江成为集装箱货轮穿梭的航道,画家对自然的观照不可避免地染上了现代性焦虑,传统山水画中"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难以复现。
二、教育体系异化:学院体制下的笔墨传承危机
(一)素描教学的霸权化与笔墨训练的边缘化
中国高等美术教育体系的建构始于20世纪初,徐悲鸿在中央大学艺术系推行的"素描是一切造型艺术的基础"理念,深刻影响了此后百年的中国画教育。这种源自西方学院派的教学体系,将写生、解剖、透视等科学方法作为基础训练核心,而传统中国画的"临摹—写生—创作"三位一体训练体系被边缘化。
在当前美院教学中,一年级基础部的素描训练往往持续一整年,学生用铅笔在纸上反复描摹石膏像,追求光影调子的逼真效果,这种训练方式培养的是"再现客观"的能力,与中国画"以形写神"的本质要求存在根本差异。到了专业阶段的水墨人物画教学,学生虽开始接触毛笔,但往往是用素描的块面思维来驾驭笔墨,导致线条失去了"骨法用笔"的书写性,墨色缺乏"随类赋彩"的韵律感。笔者曾调研某美院中国画系课程设置,发现传统山水画的"树石法"临摹课时仅占总课时的8%,而人体素描课时占比高达35%,这种课时分配反映了教育理念的深层偏差。
(二)史论教学的知识化倾向与精神传承的断裂
中国画的传承本质上是文化基因的延续,需要通过史论学习把握传统的精神脉络。然而当前美院的史论教学普遍存在知识化、碎片化倾向,将历代画论拆解为名词解释和知识点,忽略了其中蕴含的哲学思想与创作方法论。
以《林泉高致》教学为例,多数教材仅讲解"三远法"的概念定义,而忽略了郭熙"山水者,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游者,有可居者"的空间哲学背后,是对士人精神家园的构建;讲解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时,多停留在创作方法的层面,未能深入其"一画论"中"从于心"的本体论思考。这种知识化的教学导致学生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无法将传统画论转化为创作实践的指导思想。更严重的是,史论课程与创作实践的脱节,使学生难以建立"理论——实践"的转化能力,临摹古画时只关注技法形式,而忽略了笔墨中蕴含的文人精神。
(三)创作评价体系的标准化与个性精神的压抑
当代美院的创作评价体系深受西方艺术评判标准影响,强调"创新性""视觉冲击力"等外在指标,而对中国画特有的"书卷气""金石味"等精神内涵缺乏系统的评价维度。在毕业创作评审中,评委往往更关注作品的尺幅大小、材料创新和视觉效果,而对笔墨质量、文化内涵的考察流于表面。
这种评价体系导致学生创作时倾向于追求"视觉奇观":有的在宣纸上堆砌综合材料,用丙烯颜料覆盖水墨韵味;有的将传统山水解构为几何图形,以抽象构成迎合展览机制。某美院教授曾坦言:"现在学生毕业创作,画得越像传统山水画越难获奖,反而是那些看不懂的装置式水墨更容易引起关注。"这种导向使年轻画家过早放弃了对传统笔墨的深度探索,转而寻求表面化的形式创新,导致中国画创作出现"去笔墨化"的危险倾向。
三、市场机制规训:资本逻辑下的创作生态异化
(一)符号消费与创作同质化的恶性循环
艺术市场的本质是审美价值的货币化体现,但当代中国画市场却陷入了符号消费的怪圈。画廊与拍卖行倾向于推广具有明确视觉符号的艺术家,如"泼墨山水""熊猫题材""京剧人物"等,这些符号经过市场反复炒作,形成固定的消费认知,导致画家为迎合市场需求而固化个人风格。
部分画家的成名作品,原本是艺术家个性化的创作符号,但在市场推动下被无限复制,形成流水线式生产。这种创作同质化不仅导致艺术价值的贬值,更严重的是扼杀了艺术家的探索精神。某知名画廊负责人曾透露:"我们签约画家时,首先要求他们有明确的视觉符号,这样便于市场推广,那些不断尝试新风格的画家,反而很难获得资本支持。"这种市场逻辑使许多画家主动放弃风格探索,在符号重复中走向创作枯竭。
(二)展览机制的视觉化导向与精神深度的消解
当代艺术展览体系深受西方策展理念影响,强调展览的视觉冲击力和叙事完整性,这种导向深刻影响了中国画的创作方向。全国美展等权威展览中,大幅作品往往比小幅作品更易入选,导致画家纷纷采用丈二巨幅创作,为填满画面而堆砌元素,失去了传统中国画"计白当黑"的空间智慧。
在主题性创作中,展览机构常预设明确的叙事框架,要求画家将历史事件或现实题材转化为视觉图像,这种创作模式迫使画家放弃个人化的精神表达,转而追求宏大叙事的视觉图解。2019年某重大历史题材创作工程中,多位山水画家被要求在作品中加入具体历史人物,导致传统山水画的意境营造让位于情节叙事,笔墨沦为图解主题的工具。这种展览机制使中国画逐渐失去了"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特质,沦为视觉叙事的附庸。
(三)价格体系的泡沫化与艺术价值的倒置
当代中国画市场的价格体系存在严重的价值倒置现象。拍卖市场上,画家的社会职务、曝光度等非艺术因素往往比作品本身质量更能决定价格。省级美协主席的作品价格可能数倍于潜心创作的学院派画家,这种"头衔定价法"导致艺术价值判断标准的严重扭曲。
更值得警惕的是,金融资本的介入使中国画成为投资理财产品,部分画家与机构合谋制造虚假成交记录,通过拍卖行自买自卖抬高价格,形成市场泡沫。以高价成交,创当时纪录,多数为机构操盘的虚假交易。这种泡沫化运作使艺术市场脱离了审美本质,画家创作的首要目标从艺术探索异化为价格炒作,严重破坏了创作生态的健康发展。
四、技术伦理困境:数字时代的笔墨本体危机
(一)媒介技术的扩张与笔墨书写性的消解
数字技术的发展为艺术创作带来了新可能,但也对中国画的笔墨本体构成了根本挑战。喷墨打印技术可以精准复制黄宾虹的积墨效果,3D建模软件能够生成虚拟的山水空间,这些技术使传统笔墨的独特性受到质疑。更有甚者,部分艺术家利用计算机程序生成水墨效果,通过算法控制墨色浓淡和线条走向,使创作过程失去了"心手相应"的生命体验。
在实验水墨领域,喷枪、刻刀、拓印等非传统工具的广泛使用,虽然拓展了水墨的表现形式,却也导致笔墨丧失了书写性的本质。传统毛笔的弹性与运笔的提按顿挫,是画家心性节奏的直接体现,而机械工具制作的肌理效果,无论多么精美,都缺乏"笔断意连"的精神气韵。徐冰的《芥子园山水卷》通过数控机械复制传统山水,虽在观念上具有批判性,却也从反面印证了机械复制无法替代笔墨中的生命温度。
(二)图像复制与原创精神的稀释
互联网时代的图像爆炸式传播,使画家的视觉资源获取变得前所未有的便捷,但也导致创作中的原创性被稀释。画家通过搜索引擎获取素材,在Photoshop中拼贴组合,这种创作方式使作品沦为图像的二次加工,失去了"外师造化"的直接体验。
更严重的是,图像复制导致风格的快速同质化。当某类水墨风格在社交媒体上流行后,短时间内就会出现大量模仿之作,形成"网红水墨"现象。2020年某短视频平台流行的"禅意水墨",实则是将传统文人画的简笔造型与现代设计元素拼贴,这种快餐式创作缺乏文化深度,却因符合大众审美趣味而广泛传播,进一步挤压了严肃创作的生存空间。
(三)虚拟体验与自然观照的隔阂
VR技术的发展使"虚拟山水"成为可能,观众可以通过头戴设备"进入"计算机生成的山水空间,这种虚拟体验虽然新奇,却替代不了传统山水画中"澄观万象"的精神体验。传统画家"行万里路"的写生过程,是身体与自然的深度对话,而虚拟技术构建的视觉景观,本质上是数据化的视觉符号,缺乏自然山水的生命气场。
在教学领域,部分院校尝试用VR技术替代实地写生,让学生在虚拟环境中"观察"山水,这种方式虽然解决了教学成本问题,却失去了"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的审美体验。中国画的笔墨语言本质上是对自然生命节奏的视觉转化,缺乏实地观照的创作,必然导致笔墨失去与自然的精神联结,沦为技术化的视觉游戏。
五、心性复归:笔墨本体的现代性重构
(一)心性哲学的当代诠释与笔墨本体论重建
重构当代中国画的笔墨体系,需要回归"心性—笔墨"的传统哲学根基,并赋予其现代诠释。王阳明"心外无物"的哲学思想,可以转化为当代创作中"从于心"的精神自觉;宗白华"艺境"理论中"主观的生命情调与客观的自然景象交融互渗"的观点,为构建现代笔墨语言提供了理论支撑。
当代画家需要重建"笔墨即心性"的本体论认知。吴冠中晚年在《笔墨等于零》中修正观点:"脱离了具体画面的孤立的笔墨,其价值等于零",实则强调了笔墨与心性表达的不可分割性。李可染"用最大的功力打进去,用最大的勇气打出来"的创作理念,正是对传统笔墨心性论的现代诠释——先通过深度临摹体悟传统笔墨的精神内核,再以个人心性转化为现代语言。这种本体论重建不是简单的传统复归,而是在现代性语境中重新确立笔墨作为精神载体的核心地位。
(二)临摹——写生——创作的现代转化机制
传统中国画的"临摹——写生——创作"体系,在当代需要建立新的转化机制。临摹不应停留在技法模仿,而应是与古人进行精神对话的过程。黄宾虹临古画"遗貌取神",通过笔墨节奏体悟古人的心性状态,这种临摹方式值得当代画家借鉴。在数字时代,临摹可以结合高清图像技术,但更重要的是通过原迹观摩(如故宫博物院的古画特展)感受笔墨的物质性存在。
写生需要超越对景描摹,发展为"心性观照"的现代形式。傅抱石"抱石皴"的形成,源于他对金刚坡云雾气象的精神感应,而非客观描绘;李宝林的"高原皴"则是将青藏高原的雄浑气势内化为笔墨语言。当代写生应鼓励画家在自然中寻找与个人心性契合的精神符号,用现代视觉经验转化传统皴法。例如,画家可以从城市建筑的几何形态中提炼新的线条语言,从工业景观的金属质感中探索墨色的现代表达,和方向作品。
创作环节需要重建"意在笔先"与"随机生发"的辩证关系。传统"胸有成竹"的创作模式在当代可以与即兴创作相结合,既要有整体的意境构想,又要保留笔墨在宣纸上自然渗化的偶然性。刘国松的"拓墨法"虽借鉴西方抽象表现主义,却通过控制水墨渗化的过程,保留了"中得心源"的创作本质,这种探索为现代创作机制提供了有益参考。
(三)文人修养体系的当代建构
中国画的精神高度历来依赖于画家的人文修养,当代画家需要重建适合现代语境的文人修养体系。这一体系应包括三个维度:传统文化的深度学习、现代知识的广泛吸纳、生命体验的深度沉淀。
在传统文化学习方面,画家不仅要研习画史画论,更应深入经史子集的核心思想。黄公望《富春山居图》的笔墨具备儒家道家的气息,这种哲学层面的文化浸润,正是当代画家普遍缺乏的。建议画家系统研读儒道释《论语》《周易》《道德经》《坛经》等经典,将其中的哲学思想转化为画面的构成法则和笔墨韵律。
现代知识的吸纳包括对西方艺术理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的广泛涉猎。吴冠中对形式美的研究,借鉴了康定斯基的抽象理论;刘万鸣的工笔作品“意笔精微”融入了“工写”的思维方式,这些案例表明,现代知识的介入可以拓展传统笔墨的表达边界。画家应避免对西方理论的简单套用,而应通过消化吸收形成新的文化视野。
生命体验的深度沉淀尤为重要。齐白石"衰年变法"的成功,源于他对乡间生活的深厚情感;黄胄的新疆题材创作,得益于他长期与牧民生活在一起。当代画家需要走出画室,在城市化进程中捕捉新的生命体验,在科技时代保持对人性本质的思考。这种体验不应停留在表面观察,而应转化为对时代精神的深层把握。
六、人文蕴养:作品灵魂的生成机制
(一)诗书画印的现代统合与意境营造
传统中国画"诗书画印"的综合修养,在当代需要进行现代性转化。题画诗不应简单模仿古人平仄,而应结合现代诗歌的语言特质,表达当代人的精神感受;书法学习也不应局限于碑帖临摹,而应探索书法线条与现代设计构成的融合可能。
吴昌硕将石鼓文的笔法融入绘画,形成"以书入画"的独特风格;潘天寿的题画诗常以哲学思考入题,提升了画面的精神深度。当代画家可以借鉴这种思路,例如在都市题材作品中融入现代诗的碎片化语言,用书法线条表现城市建筑的节奏韵律。印章艺术也可突破传统篆法,吸收现代图形设计理念,形成具有时代特征的视觉符号。
(二)跨文化语境下的人文资源整合
在全球化语境下,中国画的人文蕴养需要整合多元文化资源。这不是简单的中西拼接,而是在深层文化逻辑上的对话与融合。林风眠将敦煌壁画的色彩与西方现代主义形式结合,创造出兼具东方意境与现代美感的新图式;赵无极从《周易》哲学出发,将传统山水精神转化为抽象绘画语言,这些探索为跨文化整合提供了范例。
当代画家可以从更多元的文化资源中汲取营养:从非洲雕刻的造型张力中强化线条的表现力,从日本茶道的"和敬清寂"中体悟画面的空寂意境,从印度哲学的"梵我合一"中深化对天人关系的思考。这种整合需要建立在对本民族文化的深度理解之上,避免陷入文化拼贴的表面化陷阱。
(三)时代精神的个体性表达与普遍共鸣
优秀的艺术作品必然蕴含着时代精神,但这种表达需要通过个体生命体验来实现。李可染的"红色山水"将革命情怀融入传统山水,傅抱石的"风雨山水"则折射出抗战时期的民族精神,这些作品之所以具有感染力,在于画家将时代精神转化为个人化的笔墨语言。
当代画家需要在城市化、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寻找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主题。例如,对生态危机的关注可以转化为山水画的新意境,对科技伦理的思考可以通过水墨媒介进行视觉表达。这种表达不应是概念化的图解,而应像齐白石画虾、徐悲鸿画马一样,通过具体的艺术形象和独特的笔墨语言,实现个体体验与时代精神的深度融合。
七、破局之路:构建生态化的创作体系
(一)教育体系的重构:从技术训练到文化传承
高等美术教育需要重建以文化传承为核心的教学体系。建议在美院中国画系设立"笔墨本体"基础课程,将书法训练、古画临摹作为一年级必修课,改变目前素描一统天下的局面。中央美院中国画学院近年推行的"传统造型基础"教学改革,将白描、书法与素描结合,是值得推广的探索方向。
史论教学应打破知识化倾向,建立"理论—实践"的互动机制。可以借鉴日本艺术院校的"画论临摹"教学法,让学生不仅研读画论,更用笔墨实践来验证画论观点。例如,学习"气韵生动"时,通过临摹不同时期的作品,体会气韵在笔墨中的具体呈现;学习"骨法用笔"时,通过书法练习理解线条的骨力内涵。
(二)市场机制的调整:建立多元价值评价体系
艺术市场需要打破单一的符号消费逻辑,建立多元的价值评价体系。画廊与拍卖行应承担更多的文化责任,不仅推广具有市场潜力的作品,更要引导收藏者关注笔墨质量和文化内涵。建立中国画的"笔墨传承"认证体系,对坚守传统笔墨精神的艺术家给予市场认可。
展览机制需要改变唯视觉化的导向,为不同类型的创作提供展示空间。除了大型综合性展览,应增加以笔墨研究为主题的小型展览,如"传统皴法现代转化"展、"书法入画"专题展等,形成对笔墨本体的学术探讨氛围。策展人应提升对中国画文化内涵的理解,避免用西方当代艺术标准简单评判中国画作品。
(三)创作生态的自我修复:建立心性修炼机制
画家个体需要建立适合现代生活的心性修炼机制。可以借鉴传统文人的"日课"制度,每日安排固定时间进行书法练习、经典研读和静观思考,保持精神的集中与纯粹。黄宾虹晚年每日临池不辍,即使失明后仍坚持摸索笔墨,这种对艺术的虔诚态度值得当代画家学习。
建立"创作共同体"也是修复创作生态的有效途径。画家可以组成小型研习团体,定期进行作品研讨、古画临摹和集体写生,在同行交流中相互启发、共同提高。历史上"海上画派"、"岭南画派"的形成,都与画家群体的互动交流密切相关,这种传统在当代仍具有生命力。
结语:在传统与现代的张力中寻找笔墨的未来
当我们审视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中那看似随意却蕴含宇宙秩序的笔墨时,当我们感受八大山人鸟眼中那穿透时空的孤寂目光时,不得不思考:当代中国画究竟失去了什么?或许不是技法的失传,而是那种将生命体验转化为笔墨语言的精神自觉。在数字技术重构视觉经验的时代,在全球化导致文化认同危机的语境中,中国画的破局之路不在于形式的创新,而在于心性的复归——回归到"外师造化,中得心源"的创作本质,回归到"笔墨当随时代"的精神自觉。
这不是简单的传统复兴,而是需要画家在现代性体验中重新发现自然、观照内心。当我们能用传统的笔墨语言表达对智慧城市的思考,能用"气韵生动"的审美标准评价数字艺术时,或许才能真正实现中国画的现代转型。最终,决定一幅作品是否具有灵魂的,不是媒介材料的新旧,而是画家是否在笔墨中倾注了真实的生命体验和深沉的人文思考。在这个图像泛滥而精神匮乏的时代,唯有回归心性、滋养人文,才能让中国画的笔墨重新成为照亮心灵的光。
2025年5月于云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