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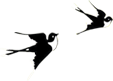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当前位置:首页 -- 学术论坛 摘 要
本文以宋明心性学为理论基础,系统考察中国传统绘画风格的自然形成逻辑,揭示其"心体——技法——意境"三元统一的创作本体论。通过对比分析徐渭《墨葡萄图》等经典案例与当代设计化创作的范式差异,论证设计思维对中国画"通会内涵"与"写意精神"的消解。研究表明:传统风格形成遵循"澄心观物——以意使笔——通会融贯"的心性实践路径,而设计化创作因陷入"机心先动——形式预制——技术异化"的现代性困境,导致艺术精神的本体性失落。重建当代绘画的精神根基,需回归心性学"心手相应"的创作伦理,在技术理性中重构"意境生成"的哲学维度。
一、心性学视域下的绘画创作本体论建构
(一)哲学根基:从"心统性情"到"心外无物"的理论推演
心性学作为宋明理学与心学的核心范畴,为传统绘画提供了独特的创作本体论。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提出"心统性情",将"心"界定为认知主体与道德本体的统一,"性"为天理在人身上的投射,"情"为心性的外在发用。这种哲学框架在绘画领域转化为"心说",如郭熙《林泉高致》所言"画者,心印也",将画面视为创作者心性的视觉显影。王阳明进一步提出"心外无物",将艺术创作界定为"心体"的即时外化——当创作者通过"致良知"的修养功夫使心性达至澄明之境,笔墨便会遵循"心"的内在秩序自然流淌,形成"无法法"的风格特征。
这种创作逻辑根本区别于西方模仿论,强调风格形成的非预设性。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描述的"宇宙在乎手"的创作状态,实则是心性学"万物皆备于我"在艺术领域的具象化——画面的笔墨韵律、构图秩序、意境营造,皆为创作者"心体"与"性理"互动的即时产物,而非技术规则的刻意堆砌。徐复观在《中国艺术精神》中指出,这种创作机制的本质是"由人格根源所流出的艺术精神",与庄子"解衣盘礴"的自由创作状态一脉相承。
(二)画论互证:"通会"概念的哲学阐释
中国传统画论中的"通会"范畴与心性学形成理论共振。张彦远《历代名画记》提出"若不知师资传授,则未可议乎画",但将"通会"的终极境界界定为"师资"与"心源"的辩证统一。吴道子学书于张旭、贺知章,最终形成"莼菜描"的独特笔法,其"笔迹遒劲,如磔怒猊"的线条张力,实为"心潮即笔潮"的心性外化。这种"通会"并非技法的简单融会,而是如朱熹"理一分殊"所阐释的"心性——技法——意境"在"理"的统摄下达成多元合一:
技术层面体现为"化繁为简"的笔墨自觉;
学养层面呈现为"诗书画互通"的综合建构;
心性层面实现为"天人合一"的精神超越。
二、传统绘画风格自然生成的三重心性机制
(一)"澄心观物":创作准备阶段的心性修养
心性学认为"心"的本然状态是"虚灵不昧",但世俗功利会使其遮蔽。创作前的"澄心"过程,即通过"居敬""省察"等修养功夫,使心性回归"空明"。米芾画云山前"斋心三日"的行为,本质是通过心性净化,让"心体"与"物态"达成自然感应——其"米点皴"的朦胧氤氲,并非对自然山水的客观描摹,而是"心与云俱闲"的状态外化。
这种"观物"机制具有鲜明的王阳明哲学特征:"意之所在便是物"。徐渭创作《墨葡萄图》时,"笔底明珠无处卖"的愤懑心绪,使墨色的浓淡干湿成为心性的宣泄载体,藤蔓的缠绕扭曲实为生命体验的视觉转译。文徵明强调"写兰需备四时之气",其本质是要求创作者通过长期的心性观照,使物象提炼超越外形模仿,达至"物我交融"的境界。
(二)"以意使笔":创作过程中的即时生成逻辑
在自然生成的创作中,"意"非预设的形式规划,而是心性在当下的直觉显现。黄公望作《富春山居图》"兴之所至,逐笔添加"的创作方式(《富春山居图·题跋》),使其长披麻皴的疏松淡远成为"心随江水流"的节奏外化;倪瓒"折带皴"的方硬简淡,暗合其"胸中逸气"的孤介心性。这种生成机制的核心在于"心不滞于物":八大山人画鱼鸟"白眼向人"的变形处理,以夸张突破物象束缚,使技法完全服务于"意"的表达;徐熙"落墨为格"的没骨法,以水墨晕染的随机性呼应"心体"的流动感,达成"笔所未到气已吞"的意境。
王阳明描述的"如舟之掌舵,平手执之,自由去来,皆不费力"的实践状态,恰是"以意使笔"的最佳注脚——笔墨运动与心性节奏达成同频共振,形成"心手双畅"的创作境界。
(三)"通会融贯":风格圆成阶段的哲学化合
真正的绘画风格是"师资传授"与"心源独创"的辩证统一。沈周早年师法王蒙,中年融入吴镇笔意,晚年形成"粗沈"风格,其阔笔重墨的背后是"出入宋元,自抒胸臆"的心性成熟。这种"通会"的圆成体现为三重境界:
1. 技法层面的"法理合一":董源将披麻皴的圆浑与点子皴的苍茫融合,使笔墨既合"理"(自然山水的结构规律)又显"法";
2. 学养层面的"道艺互通":赵孟頫以"石如飞白木如籀"的书法用笔入画,实现"道"(书法哲学)与"艺"的本体论统一;
3. 心性层面的"天人合一":文徵明画中"书卷气"的呈现,实为"士君子"道德修养与艺术创作的化合,如徐复观所言,是"人性与艺术精神的共同完成"。
三、设计化创作对传统精神的消解——以中国画为中心的考察
(一)"机心先动":设计逻辑对心性本真的遮蔽
现代设计思维的介入使中国画创作陷入"机心先动"的困境,创作者以市场需求、展览标准或学术范式预先设定风格框架,导致"心体"被功利性目的遮蔽,具体表现为四重割裂:
1. 符号拼贴对"澄心观物"的背离
传统绘画的物象提炼源于"澄怀观道"的长期体悟,如石涛"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创作准备。而设计化创作中,梅兰竹菊等传统意象被简化为可复制的视觉符号:如某些画家"机械套用兰花"四叶攒茎"的程式,叶片俯仰失去"各随其心"的生机,沦为设计素材库中的"标准件"。这种创作背离了文徵明"写兰需备四时之气"的观物之道,恰如王阳明批判的"务外遗内,博而寡要",使徐渭式的生命宣泄沦为形式表演。
2. 预制构图对"经营位置"随机性的消解
中国画"经营位置"本是"心随笔运"的即时建构,黄公望《富春山居图》"逐笔添加"的散点构图实为"心随江水流"的节奏外化。设计逻辑却将其转化为标准化模板:当代部分山水画遵循"近景树石+中景屋舍+远景云山"的三段式结构,甚至套用西方绘画的"黄金分割"法则,将"虚实相生"的随机性压缩为可计算的视觉比例。美展中工笔人物画大量采用对称式构图与中心透视,将顾恺之"迁想妙得"的意象空间降维为设计图纸般的秩序化场景,丧失倪瓒"一河两岸"留白中"境由心造"的写意精神。
3. 技术依赖对"心手相应"整全性的割裂
传统绘画"笔墨"是心性与技法的合一,如吴道子"莼菜描"的顿挫源于"当其下手风雨快"的即时性。设计化创作中,数字工具与预制技法导致"心手分离":部分创作者先用CAD绘制山水轮廓,再以喷绘处理水墨层次,最后人工添加皴法细节,将"一笔而成"的笔墨过程拆解为工业化流程。更有甚者使用"皴法模板"拓印山石纹理,使范宽"雨点皴"中"心与山齐"的苍茫意境沦为技术展演,印证石涛"无法而法,乃为至法"的警示。
4. 市场导向对"画为心迹"本真性的异化
当代中国画市场的消费逻辑催生"风格标签化"倾向。某些画家为强化辨识度,将个人风格简化为固定图式:重复某类荷花瓣的勾勒弧度、统一某类山石的皴擦方向,形成类似设计品牌的"视觉标识"。这种创作背离沈周"出入宋元,自抒胸臆"的心性成熟路径,如朱熹批判的"小有所得,则欣然自喜",使画面丧失"由人格根源所流出的艺术精神"。
(二)案例解构:《溪山行旅图》与设计化山水的精神裂隙
范宽创作时"危坐终日,纵目四顾",其"雨点皴"的密集排布是终南山肌理与内心震撼的同频共振,每一笔皴擦都蕴含"心性——视觉"的即时互动。而现代某景区定制画作采用以下流程:
1. 电脑生成山体结构线;
2. 按色谱标准填充石青石绿;
3. 批量复制"披麻皴"笔刷;
4. 机械添加流水、点景人物。
画面虽符合"青绿山水"的视觉定义,却失去"山性即我性,山情即我情"的观照深度,(唐志契《绘事微言·山水性情》)。范宽笔下"山欲高,烟霞锁其腰则高矣"的气韵营造,在设计逻辑中被简化为"留白比例=30%"的技术参数,"理气合一"的哲学建构沦为视觉设计指标。这种异化的本质,是设计思维将中国画从"心性生成系统"异化为"形式制造系统"。
四、对比研究:从心性生成到设计化创作的风格本体差异
(一)自然生成案例:徐渭《墨葡萄图》的精神完整性
徐渭以破笔泼墨写葡萄藤,线条跌宕与墨色渗化完全随情感起伏:藤蔓缠绕如狂草飞白,叶片浓淡似心绪浓愁,题诗"笔底明珠无处卖"直接将心性注入画面。在此创作中,"皴法""墨法"等技法概念被消解,代之以"心手双畅"的即时表达,恰如王阳明所言"平手执舵,自由去来"的实践状态,实现风格形成与心性本真的绝对统一。艺术史学者方闻指出,此类作品的"笔墨运动轨迹"实为"心灵轨迹的视觉呈现",印证了心性学"风格即心迹"的理论预设。
徵明画中"士气"、陈洪绶笔下"高古"的精神内涵,在当代绘画设计中难以看到。正如方东美批判的,现代人的心灵已被"技术理性碎片化",难以实现心性与形式的深层通会。
五、结论:
技术时代"心性——风格"生成伦理的重建路径生,设计划创作对传统绘画的破坏,本质是工业文明"理性化"思维对艺术创作"诗性智慧"的本体论挑战。从心性学视角看,当代绘画风格危机的根源并非形式创新不足,而是"心体"在技术与商业裹挟下的遮蔽与异化。重建"通会内涵"与"写意精神",需从两方面突破:
其一,重构"澄心观物"的创作伦理。宗白华指出"中国艺术是心灵间的直接对话",创作者需在技术工具之外保持"心性自觉"——回到绘画中去机心而显本真"的现代参照。
其二,重拾"以意使笔"的创作方法。传统绘画"一笔三折"的笔意、"计白当黑"的经营,本质是"心意"对"形式"的主导。当代创作可借鉴隈研吾"负建筑"的理念,以"退让姿态"实现"境意合一"——通过减法思维剔除冗余设计,让形式成为心性的自然延伸,王阳明"天地万物与人原是一体"的哲学观提示我们:当绘画风格重新成为心性的镜像,技术便不再是创作的桎梏,而成为心性的延伸工具。
这并非对传统的简单复归,而是在设计时代重建"艺术即心迹"的本体论认知——唯有如此,被技术理性抽空的"通会"与"写意",才能在当代艺术中重获精神根基。真正的绘画创新,应当如石涛所言"借古以开今",在心性学的哲学光照下,实现传统艺术精神的现代性转化。
乙巳年六月十五日于云庐